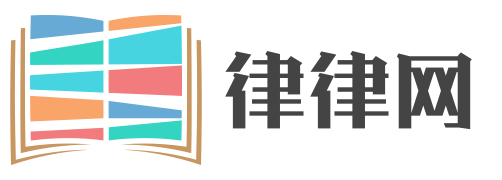“规则主义”下使用作品的“合理性”判断
发布时间:2021-05-23 02:42:15
合理使用制度虽已成为各国著作权法的通行规则,但“合理性”判断仍存在“立法上的缺憾与司法中的窘境”【1】。本文结合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简称《适用著作权法的解释》)第18条的理解,探讨“规则主义”下使用作品“合理性”判断的意义和规则,力求以理论论证解释实务困惑和引导法律适用。
一、“因素主义”和“规则主义”立法模式下的不同实践结论 虽然目前已确立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国家在著作权立法中大多设有合理使用规定,但立法内容和立法模式各不相同。就立法模式而言,主要有“因素主义”和“规则主义”两种。 (一)“因素主义”下“合理性”构成作品合理使用的必要因素,使用作品的情形类别不具决定意义 “因素主义”立法模式以美国《联邦著作权法》第107条的规定为典型代表。该条文规定:“为了批评、评论、新闻报道、教学、学术或研究之目的而使用版权作品的,包括制作复制品、录音制品或以该条规定的其他方法使用作品,系合理使用,不视为侵犯版权的行为。任何特定案件中判断对作品的使用是否属于合理使用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包括:(1)该使用的目的与特性,包括该使用是否具有商业性质,或是为了非营利的教学目的;(2)该版权作品的性质;(3)所使用的部分的质与量与版权作品作为一个整体的关系;(4)该使用对版权作品之潜在市场或价值所产生的影响。作品未曾发表这一事实本身不应妨碍对合理使用的认定,如果该认定系考虑到上述所有因素而做出的。”【2】加拿大《著作权法》第17条(2)(a)也采用类似的立法模式,规定“以私人学习、研究、批评、评论或者报刊评论为目的合理利用作品”的行为不构成侵犯著作权。一种利用行为是否公平是一个事实和程度问题,必须考虑下列因素:利用的数量、利用是否具有竞争性、与被告添加的部分相比所占的比例、作品是否为未出版的作品等。【3】“因素主义”立法模式在判断某一具体的作品使用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时,是不以法律规定的特定范围或情形为前提的,而以法律规定应当予以考虑的“合理性”因素为核心。 “因素主义”根据“因素”所形成的过程又可分为“归纳主义”方式与“演绎主义”方式。【4】无论是“归纳主义”或是“演绎主义”,在现实的法律实践中,“因素主义”下已经归纳或列出的“合理性”的因素或抽象演绎的“合理性”理性标准,都仅是无形的理念指导,而非有形的界限或约束。“合理性”判断并不是按照约定俗成的标准来“对号入座”的,而是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形进行论证,论证理由或判断标准是灵活多样的。据此,在“因素主义”模式下,判断对使用作品的行为在多大的范围内属于合理使用,完全是法官解释和权衡法律因素的结果,而不存在必然的适用规则。 (二)“规则主义”下使用作品的情形类别具有决定意义,“合理性”仅是次一级的考察内容 我国《著作权法》被认为采用的是“规则主义”立法模式。采用类似立法模式的还有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等国。尽管这些国家在合理使用的一般性规定、情形范围等具体立法内容上仍存在相当的差异,但对合理使用行为的认定大多采用封闭式的规定,即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才可以主张合理使用。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的立法模式,对合理使用的规定首先框定了一个前提,即“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因此合理使用行为的判断必须在法律限定的情形范围内进行,法官不得按照一般性原则进行解释和认定。 “规则主义”源于制定法注重法律确定性之传统,慎重对待限制著作权行使的合理使用制度,对每一种合理使用的适用情形力图穷尽列举且强调清晰表述和严格界定,因而回避可以灵活、广泛解释的抽象性标准。并且,制定法的稳定性要求也使“规则主义”下的合理使用制度不便朝令夕改,从而使它处于滞后于时代变化而不停地受到诘难的窘境中。在“规则主义”立法模式下,司法能动性受到限制,法官适用法律简单而又直接,审判结果容易达到形式上的公正。但封闭式规定因法律确定性、稳定性因素决定而在动态变化的社会发展中必然产生滞后性,固定的“规则”往往不利于实质公平、合理地解决现实问题,缺乏应有的灵活性和包容性。 在“规则主义”下,就某一使用作品的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而进行的判断,首先应当考虑的是该行为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主张合理使用的情形,若不具备这一前提条件,合理使用主张便无从被采信。只有在具备了这一前提后,再对照法律条文考察是否满足法律规定的适用条件。由此,按照纯粹的“规则主义”,适用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十)项规定,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之合理使用,行为范围仅限于“临摹、绘画、摄影、录像”这四种再现作品的行为,使用对象也仅限于“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对该条文的适用不得扩大至其他类似行为,也不应对该行为做延伸性解释。 (三)改良“规则主义”,强化“合理性”判断的法律意义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我国《著作权法》关于合理使用的僵硬性规定已经引发社会生活及司法实践的许多困惑,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作品使用者及作品传播者利益平衡关系发生变化后,合理使用制度更是在许多纠纷面前显得难以适从。笔者认为,凭借法官素质发挥灵活作用并完全属于利益权衡工具的“因素主义”,并不完全适于我国的司法体制和法治土壤,因而不宜进行照搬或者改造性移植;而纯粹的“规则主义”又无法为迅速变化的社会发展提供公正、合理地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因而,有必要在不改变现有立法模式的前提下,对条文的规定进行适当的改良和修正,主要是加入润滑剂,使之更具开放性和灵活性。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增加“合理性”判断的指导性原则。正如美国众议院所指出的,“第107条之中的合理使用学说的表述提供给使用者在决定什么时候援引合理使用时的一些指导。……第107条意在再次陈述现行的合理使用司法学说,既不以任何方式改变、缩小它,也不扩大它”。【5】 在我国,借鉴美国著作权法,在保留“规则主义”的合理使用立法模式下,增设普遍适用于各类合理使用情形的一般性判断规则,对于指导正确适用具有“模糊性”的合理使用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也有助于法官在纷繁复杂、各式各样的纠纷处理中获得清晰的审判思路。 其二,在所列举的合理使用情形后增设一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合理使用情形”。这样。在不影响著作权法相当时期的稳定性的同时,可以通过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制定或修订的法规来反映合理使用制度的微观调整。如果现行的著作权法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合理使用情形”这样的“兜底性”规定,那么借助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类似的法规,就得以在保留合理使用立法“规则主义”下,解决各类社会变化引发的合理使用制度的“重构”问题。
一、“因素主义”和“规则主义”立法模式下的不同实践结论 虽然目前已确立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国家在著作权立法中大多设有合理使用规定,但立法内容和立法模式各不相同。就立法模式而言,主要有“因素主义”和“规则主义”两种。 (一)“因素主义”下“合理性”构成作品合理使用的必要因素,使用作品的情形类别不具决定意义 “因素主义”立法模式以美国《联邦著作权法》第107条的规定为典型代表。该条文规定:“为了批评、评论、新闻报道、教学、学术或研究之目的而使用版权作品的,包括制作复制品、录音制品或以该条规定的其他方法使用作品,系合理使用,不视为侵犯版权的行为。任何特定案件中判断对作品的使用是否属于合理使用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包括:(1)该使用的目的与特性,包括该使用是否具有商业性质,或是为了非营利的教学目的;(2)该版权作品的性质;(3)所使用的部分的质与量与版权作品作为一个整体的关系;(4)该使用对版权作品之潜在市场或价值所产生的影响。作品未曾发表这一事实本身不应妨碍对合理使用的认定,如果该认定系考虑到上述所有因素而做出的。”【2】加拿大《著作权法》第17条(2)(a)也采用类似的立法模式,规定“以私人学习、研究、批评、评论或者报刊评论为目的合理利用作品”的行为不构成侵犯著作权。一种利用行为是否公平是一个事实和程度问题,必须考虑下列因素:利用的数量、利用是否具有竞争性、与被告添加的部分相比所占的比例、作品是否为未出版的作品等。【3】“因素主义”立法模式在判断某一具体的作品使用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时,是不以法律规定的特定范围或情形为前提的,而以法律规定应当予以考虑的“合理性”因素为核心。 “因素主义”根据“因素”所形成的过程又可分为“归纳主义”方式与“演绎主义”方式。【4】无论是“归纳主义”或是“演绎主义”,在现实的法律实践中,“因素主义”下已经归纳或列出的“合理性”的因素或抽象演绎的“合理性”理性标准,都仅是无形的理念指导,而非有形的界限或约束。“合理性”判断并不是按照约定俗成的标准来“对号入座”的,而是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形进行论证,论证理由或判断标准是灵活多样的。据此,在“因素主义”模式下,判断对使用作品的行为在多大的范围内属于合理使用,完全是法官解释和权衡法律因素的结果,而不存在必然的适用规则。 (二)“规则主义”下使用作品的情形类别具有决定意义,“合理性”仅是次一级的考察内容 我国《著作权法》被认为采用的是“规则主义”立法模式。采用类似立法模式的还有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等国。尽管这些国家在合理使用的一般性规定、情形范围等具体立法内容上仍存在相当的差异,但对合理使用行为的认定大多采用封闭式的规定,即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才可以主张合理使用。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的立法模式,对合理使用的规定首先框定了一个前提,即“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因此合理使用行为的判断必须在法律限定的情形范围内进行,法官不得按照一般性原则进行解释和认定。 “规则主义”源于制定法注重法律确定性之传统,慎重对待限制著作权行使的合理使用制度,对每一种合理使用的适用情形力图穷尽列举且强调清晰表述和严格界定,因而回避可以灵活、广泛解释的抽象性标准。并且,制定法的稳定性要求也使“规则主义”下的合理使用制度不便朝令夕改,从而使它处于滞后于时代变化而不停地受到诘难的窘境中。在“规则主义”立法模式下,司法能动性受到限制,法官适用法律简单而又直接,审判结果容易达到形式上的公正。但封闭式规定因法律确定性、稳定性因素决定而在动态变化的社会发展中必然产生滞后性,固定的“规则”往往不利于实质公平、合理地解决现实问题,缺乏应有的灵活性和包容性。 在“规则主义”下,就某一使用作品的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而进行的判断,首先应当考虑的是该行为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主张合理使用的情形,若不具备这一前提条件,合理使用主张便无从被采信。只有在具备了这一前提后,再对照法律条文考察是否满足法律规定的适用条件。由此,按照纯粹的“规则主义”,适用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十)项规定,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之合理使用,行为范围仅限于“临摹、绘画、摄影、录像”这四种再现作品的行为,使用对象也仅限于“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对该条文的适用不得扩大至其他类似行为,也不应对该行为做延伸性解释。 (三)改良“规则主义”,强化“合理性”判断的法律意义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我国《著作权法》关于合理使用的僵硬性规定已经引发社会生活及司法实践的许多困惑,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作品使用者及作品传播者利益平衡关系发生变化后,合理使用制度更是在许多纠纷面前显得难以适从。笔者认为,凭借法官素质发挥灵活作用并完全属于利益权衡工具的“因素主义”,并不完全适于我国的司法体制和法治土壤,因而不宜进行照搬或者改造性移植;而纯粹的“规则主义”又无法为迅速变化的社会发展提供公正、合理地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因而,有必要在不改变现有立法模式的前提下,对条文的规定进行适当的改良和修正,主要是加入润滑剂,使之更具开放性和灵活性。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增加“合理性”判断的指导性原则。正如美国众议院所指出的,“第107条之中的合理使用学说的表述提供给使用者在决定什么时候援引合理使用时的一些指导。……第107条意在再次陈述现行的合理使用司法学说,既不以任何方式改变、缩小它,也不扩大它”。【5】 在我国,借鉴美国著作权法,在保留“规则主义”的合理使用立法模式下,增设普遍适用于各类合理使用情形的一般性判断规则,对于指导正确适用具有“模糊性”的合理使用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也有助于法官在纷繁复杂、各式各样的纠纷处理中获得清晰的审判思路。 其二,在所列举的合理使用情形后增设一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合理使用情形”。这样。在不影响著作权法相当时期的稳定性的同时,可以通过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制定或修订的法规来反映合理使用制度的微观调整。如果现行的著作权法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合理使用情形”这样的“兜底性”规定,那么借助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类似的法规,就得以在保留合理使用立法“规则主义”下,解决各类社会变化引发的合理使用制度的“重构”问题。
最新资讯
-
02-17 0
-
06-20 0
-
08-18 2
-
12-13 1
-
08-17 0
-
08-26 2